北京市西城区有条灵境胡同,对于经常乘坐地铁4号线的人们来说,这个地名可是再熟悉不过。常有人将“灵境”二字误写为“灵镜”,一字之差,却有不同的意味。灵境胡同,得名于当年朱棣为两位神仙建的灵济宫,后因谐音而转为“灵境”。虽说是谐音,但“灵境”所代表的“神灵仙境”之意,或许更贴合灵济宫的故事。
灵济宫,全名叫洪恩灵济宫,建于永乐十五年(1417)三月,是明朝初年北京城中皇家按时遣官致祭的寺庙之一。每年的正旦、冬至、皇帝生日,要派内阁礼部官员及一名太监,代表皇帝到灵济宫致祭;神仙的诞辰,由礼部官员致祭;平时初一、十五由本宫的道士致祭。
永乐十五年,正是北京紫禁城开始营建之年,朱棣政事旁午,为什么先要建这样一座庙?这两位神仙是什么来历?又凭什么得到后世皇帝不断“加码”的崇拜?

明成祖朱棣像
南方“神仙”千里进京?
灵济宫中祀奉的两位所谓神仙,一叫徐知证,一叫徐知谔,是兄弟二人。哥哥知证被朱棣封为“金阙真君”;弟弟知谔被封为“玉阙真君”。因为是先帝尊崇的神仙,后世皇帝则不断“加码”崇拜。正统初,徐氏伯仲又被分别加封为崇福真君、隆福真君。至成化二十二年(1486),徐知证加封为“九天金阙总督魁神洪恩灵济慈惠高明上帝”,徐知谔加封为“九天玉阙总督罡神洪恩灵济仁惠宏净上帝”。后来,实在没法再给这兄弟俩加封了,就加封他们的父母,一个是“神父圣帝”,一个是“神母元君”。
神仙本都是人变的。徐知证、徐知谔史上实有其人,是五代时南吴大将徐温的儿子。徐温,曾经收养过一个小乞丐做义子,起名为徐知诰。这个徐知诰后来取代南吴建立了南唐、做了皇帝,于是恢复了原来的李姓,即为李昪(biàn)。徐知证、徐知谔于是就成了南唐开国皇帝的“干弟弟”。那位有名的南唐后主李煜,即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作者,是李昪的孙子。按辈分,他应叫徐知证、徐知谔“干叔爷爷”。
于是就产生一个疑问:从时间上说,徐知证、徐知谔一个卒于939年,一个卒于947年,与朱棣相距四百五十余年;从空间上说,徐温父子是海州人(今江苏省连云港),一说是徐州人,李昪建立的南唐都城在江宁(今南京),这两人一生中主要活动的地点在南方,与北京相距两千里;朱棣为何要在北京建一座庙还如此虔诚地祀奉他们二人呢?各种史料记载不一。
据明《太宗实录》记载,朱棣听说福建闽县(今福州)有座祭祀徐知证、徐知谔的灵济宫,有求必应,特别灵验,就派人去求医问药,很有奇效,于是就命人前往福建闽县,将当地的灵济宫修葺一新,为两位神仙重塑金身,同时还在北京皇城之西为其立庙,并分别加封兄弟二人为金阙、玉阙真君。
在《明史·袁忠彻传》中,又是这么说的:礼部侍郎周讷从福建回来,说闽人祀奉南唐的知谔、知诲(按:名字不一样,原文如此),其神最灵。“帝命往迎其像及庙祝以来,遂建灵济宫于都城。”
这两条大不一致的记载都语焉不详,难以化解我们的疑问。
据《帝京景物略》说,朱棣曾经患病,梦见两位道士前来授药,不日病愈。朱棣甚为感激,下令为其建宫祀——这个说法也经不住推敲。试想,谁会在梦中遇见两个不相干、不认识的人?
福建道士举荐老家神仙
问题的答案,或许也要从福建人那里寻找。陈明鹤是明朝时的一位福建人,在他所著的《晋安逸志》有这样一段记载:“男子曾甲,世居闽县金鳌峰下灌园,园中有破祠,其神尝栖箕,自称兄弟二人,南唐徐知诰之弟知证、知谔也,晋开运二年(945)率师入闽,秋毫无犯,闽人祈我于此。自是,书符疗病验若影响。永乐间,成祖北征不豫,诏曾甲入侍,运箕有验,遂……敕有司建庙。”
这就是说:朱棣的手下有个叫曾甲的福建人,原来在家种菜。他家的菜园子里有个破庙,庙里供着两位神仙。曾甲能让这两位神仙“附体”,用扶乩的方法为人治病。有一天,朱棣在外率兵打仗时病了,让曾甲为他扶乩请神,治好了朱棣的病。曾甲就告诉朱棣说,他“请”来的神仙是徐知证、徐知谔兄弟。这两位神仙栖身于他老家的菜园子里的一个破庙里。因为这兄弟二人曾经带兵入闽缉盗,所到之处秋毫无犯,当地百姓感激,于是在金鳌峰之下为他俩立了一座庙,称其为“真人”,即得道的仙人。
扶乩,也叫扶箕、扶鸾。最初是一种巫术,后来成为道教中的一种请神方式。扶乩人声称自己被神仙“附体”,“自动”写出的字或者画出的图案,是来自神仙的旨意——这当然是骗人的,扶乩人写的字,都是事先构思好的。
看来是这么回事:朱棣因为相信了这个荒诞的故事,战事结束之后,便派礼部官员去福建调查核实。礼部官员回来说:当地确实有这么两个神仙,很灵!于是朱棣下令:去福建,把那两位神仙请到北京来!这才建了灵济宫,并分别加封两位“真人”为“金阙真君”和“玉阙真君”。
在明朝人黄瑜的《双槐岁钞》中,也记载有曾甲这个人物。曾甲大名叫曾辰孙,原先是个道士,会扶乩。朱棣问什么事情,“祷祠辄应”;有病问神,“神降鸾书药味,如其法服之,每奏奇效”。于是曾辰孙大受宠信。既然会扶乩、请神,自然不用再种菜了,这一点倒是与陈明鹤的记载不矛盾。
朱棣对于这两位真君神仙别提多虔诚了。灵济宫里的两个真君塑像是木胎的,“有机可以伸缩”——胳膊、腿的关节都能活动。为什么呢?因为季节变换,要给神仙更换袍服,胳膊、腿若不能活动,这袍服怎么能给神仙穿上身?北京建了新的宫观,福建的旧祠也被修葺一新,而且规模宏大,配备了道士供奉香火。朝廷每六年派官员专程去一趟福建,去给两位大仙更换新朝服。
上有所好,下必甚之,一时节,祀奉二徐的灵济宫遍及天下,香火奇盛。
灵济宫成了朱棣的“医院”
自打北京建了灵济宫,朱棣生病不再找医生,一概遣人去灵济宫求问真君吃什么药,由道士扶乩开出“神药方”来服用。《明史》中就是这么记载的:“帝每遘疾,辄遣使问神。庙祝诡为仙方以进。”所谓神仙附体当然是骗人的,药方其实是道士开的。那道士哪懂什么药性药理、四法八纲,开出的药多是热药。朱棣服用之后“痰壅气逆,多暴怒,至失音”。大臣们谁也不敢谏阻,唯恐朱棣暴怒之下动辄杀人。
朱棣跟前有个相士叫袁忠彻,直言对朱棣说:“陛下现在痰火旺盛逆行,连话都说不出来了,这是服用灵济宫开出的符药所造成的。那符药不能再服了!”
朱棣怒道:“不服仙药,反倒服凡药不成!”袁忠彻伏地叩首,哭着央求朱棣,那些药有害无益,不能再吃。他这一哭,朱棣身边的两个小太监也哭了。朱棣更怒了:“忠彻哭我,我是要死了么?”命人把两个小太监拉出去打。袁忠彻吓坏了,连忙跑出去跪在了阶下,过了好半天才得到了朱棣的饶恕。
袁忠彻的父亲袁珙,也是一位相面先生。当年就是袁珙给道衍(即姚广孝)相的面,说道衍三角眼,像一只病虎,注定嗜杀成性,是刘秉忠一类的人。道衍听了非常高兴,认为他说得很对。道衍被朱棣带到北平后,就把袁珙推荐给了朱棣。据说袁珙根据人的形状气色,再参考出生年月日,预测命运境况“百无一谬”。据《明史》中记载,袁珙第一次来北平,朱棣找了跟自己年龄长相差不多的九个卫士,在一起拿着弓箭在酒肆中喝酒。袁珙径直走到朱棣面前跪下说:“殿下为何轻身至此?”另外九人笑着说:“你弄错了!这不是燕王。”袁珙坚持说没有认错。朱棣笑了,把他带回府中,他给朱棣相面说:“您是一位太平天子也。四十岁后,髯鬚过脐,即登大宝。”朱棣怕这些话泄露出去,把他打发走了。
今天来分析这事:袁珙是道衍举荐来的,难保不是得到了道衍的暗示和嘱托。
后来,朱棣夺取了皇位,便把袁珙召了回来,因为他当初的预测应验了。朱棣因此更加相信袁珙,在选谁继承皇位的问题上,朱棣有些拿不定主意,经袁珙相面后,才选定了后来的仁宗朱高炽、宣宗朱瞻基父子。
袁珙在永乐八年就死了,他的儿子袁忠彻从小长在燕王府,并且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,也以相面术博得了朱棣的信任。但是这回,朱棣没有接受他的忠告。
朱棣活了六十四岁,猝死于征战途中,跟他服用道士的符药不无关系。
明朝香火极盛 清朝不再承认
朱棣之后的皇帝对灵济宫两位神仙的祭祀更加虔诚。除了每月的初一、十五以及元旦、冬至、万寿圣节(皇帝生日)和两位神仙的诞辰“俱有祭祀”之外,“时食、献新”供奉不断。四时的大红纱罗纻丝织锦云龙朝服、皮弁冠之外,后世又加了平天冠、明黄纱罗纻丝衣服。黄服五年一换新,红服十年一换新,旧服焚化。北京如此这般,还要派人前往福建再如此这般。有大臣说,如此频繁地祭祀“不无烦渎”——太繁琐了!
弘治元年,礼部尚书倪岳上疏请正祀典、废诸淫祀。他在疏中说,按正史所载,五代时的徐温误国、专权、弑主,养子徐知诰篡位,知证、知谔乃叛臣之子,有何功德?称帝称君、享受隆名、接受奉祀,“僭拟益甚”,太过分了!应该降低封号、废除永乐以后的祭祀。但因为这两位大仙是成祖文皇帝敕封的,孝宗皇帝不敢改动。
明世宗朱厚熜崇信道教,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间,在灵济宫多次举行传道讲学活动,主持人是大学士徐阶、礼部尚书欧阳德、兵部尚书聂豹、礼部侍郎程文德等,“皆有气势”,“学徒云集至千人”。
明朝皇帝对灵济宫的崇拜一直延续到崇祯年间,有大臣上疏说,徐知证、徐知谔乃叛臣之子,不应接受大臣的跪拜。崇祯皇帝这才让人把两个“真君上帝”用帐子遮盖起来。
灵济宫今已无存。当年的建筑规模到底有多大难以确考。据记载,明朝时,每有大朝会,“百官习仪于此”——满朝文武都在此排练朝仪,来听道士讲学的有上千人,估计那大殿跟奉天殿大小相差不多。
后人也考证过:徐知证、徐知谔的足迹根本就没到过福建。所谓“尝帅兵入闽靖盗、秋毫无犯”之功德,纯属无稽之谈。而且,这两个人人品低劣,尤其徐知谔更是个“好珍异物,所蓄不可计”,穷极享乐一生的“狎昵小人”;二徐亦无任何信奉道教之举,既无师承,又无弟子,与道教全不相干。正如明人刘侗所言“二王皆不至闽及燕,亦不闻雅言道术”,只是“其殁也,则为神明”。看来,二徐成为道教神明,全是人为制造的;洪恩灵济宫实为“淫祠”。
清朝统治者不再承认二徐为神仙。据陈宗藩《燕都丛考》,灵济宫到清代已废。
灵济宫没有了,留下了一条“灵境胡同”。
(原标题:灵济宫的故事)
来源:北京晚报 作者宗春启
流程编辑:u099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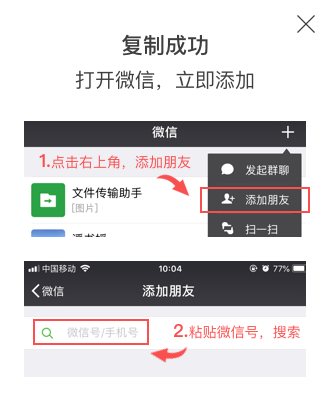
网友评论
最新评论